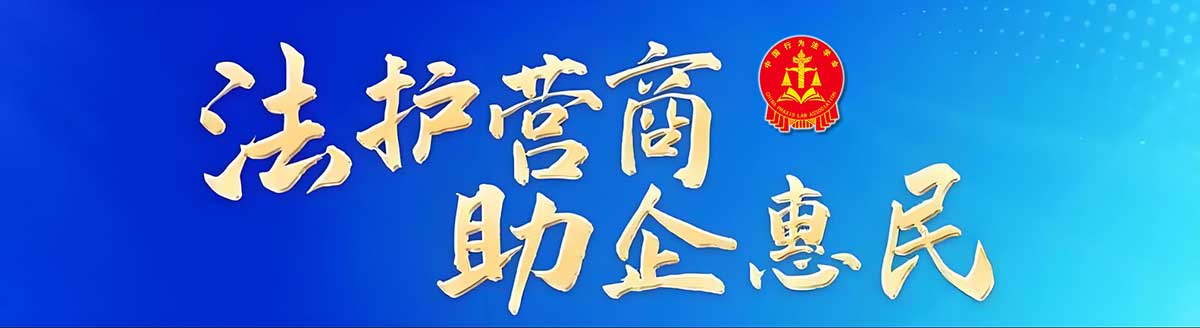7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景汉朝在出席由中国行为法学会、中南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法治实施报告(2024)》发布会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法治实施”专题研讨会上发表《深化法治改革之出路》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摘要。

《中国法治实施报告》已经连续12年,如此坚持,实属不易,令人钦佩。主创团队以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为研究对象,把握法治历史脉络,提炼法治发展规律,对我国法治中国建设进行了全面、系统、详实、连贯的记录和讲述,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记录了我国法治建设取得的划时代进展,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法治智慧,不仅对实务界和学术界有重要参考意义,一直坚持下去,也会在我国法治建设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时间越长越能彰显其史料价值。即将发布的报告体系完整,内容详实,数据和资料丰富,研究方法多元,材料的抓取、评估方法的选择等比较客观科学,值得赞扬和借鉴。
下面我谈谈法治改革如何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当前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如何进一步深化法治改革,是我们面临的一项新课题。我主要讲“六个深化”。
一、在认识国情上深化
现在大家都在谈国情,我觉得国情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如果仅仅泛泛地讲国情,法治改革将难以继续深化。如“大国且单一制”的特殊国情,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权力运行模式、立法体制、司法体制等都有深刻的影响。
以立法司法体制为例,世界上小国一般采用单一制,大国一般采取联邦制。领土面积最大的7个国家,只有中国是单一制,其他全部是联邦制。人口最多的前10位国家当中,只有中国和印尼是单一制,其他全部是联邦制。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立法体制不可能像单一制小国那样,上下完全一体,中央统一立法;也不可能像联邦制大国那样,各省(他们叫州、邦)有自己的独立的立法权,有的还有自己的宪法。所以说,我们就形成了多级立法、多主体立法的多元而且有限制的立法体制。不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立法权,地方省级、市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有立法权,其他相关部门则可以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等等。
司法体制则是统属中央事权,分级产生机构,各自任免人员,只对同级人大负责,效力及于全国。换句话说,司法权是中央事权,但是法院、检察院在中央这一级是全国人大产生,地方各级是地方同级人大产生,而且是对同级人大负责。这是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体制。而且全国各级司法机关需要人大任命的人数太多,完全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命也不现实,这就是我们的国情。要深入研究地方同级人大产生并对地方同级人大负责与司法权统属于中央事权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把它阐述清楚,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第二,在把握规律上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则事半功倍,不得法则事倍功半,甚至产生副作用。我们搞法治改革一定要把握好规律。比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法治改革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又如,如何把握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各自的权力运行规律和不同特点:人大是集体行使职权;行政机关是行政首长负责制;法院是合议庭负责制,合议庭研究案件出现分歧,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而是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少数人的意见如实记入笔录。这就是贯彻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各类机关不同的权力运行模式。
再如,司法公开。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科学地推行司法公开,司法活动要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另一方面,现在是网络社会,人人都是“麦克风”,也要避免媒体过度介入干预司法甚至绑架司法,否则就会违背舆论监督的初衷,影响司法公正。我们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司法规律和媒体舆论监督规律,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第三,在破解难题上深化
现在法治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许多法治难题。比如,我国是典型的人情社会、关系社会,这对执法司法活动的影响可以说根深蒂固。人情案、关系案,甚至金钱案,绝大部分都跟这个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要完全破除几千年来形成的这种文化思想意识,恐怕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
又如“模糊文化”是我国一个特殊的文化。这是我个人起的名称,不一定准确。模糊,就是说我们的文化有个特点,特别讲究概括、中庸,不那么十分具体、严格。比如说汉语当中“也许”“大概”“差不多”“八九不离十”等等这种词汇特别多;国画不讲具象,讲意境,有“小写意”,还有“大写意”,似与不似之间为最妙,这是我们的瑰宝;我们的菜谱,西方人操作不了:“葱3段,姜4片,盐少许,花椒、大料适当,水半锅,肉1斤左右,温火慢炖。”“葱3段”,多么长,多么粗?“姜4片”,多么薄,多么厚?“温火”,何为”温”何为“急”?“慢炖”,什么是慢,什么是快?西方人一看就晕了。这种文化对法治同样有深刻影响。古代讲“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法律规定强调“疏”而不是“密”……这些对现代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也有很大影响。在“模糊文化”的地基上建设强调严格、严密、严肃的法治大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看到深化法治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
再如,在单一制国家,一般司法标准必须统一,特别是定罪量刑的标准。但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比如说,盗窃罪,到底应当是全国一个统一标准,还是不同的标准?这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理论上统一标准公正,但是实践当中,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差别太大,落后地区可能偷一个手机从社会危害性来讲就构成犯罪了,发达地区可能偷3个手机从社会危害性讲,可能也构不成犯罪。这确实是中国的难题。
第四,在推进实施上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截至目前,我们生效的各种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章等一共大概有3.48万件左右,这既彰显了立法的成效,也给推进法律实施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
一是社会的规则意识、法治意识还比较淡,法律实施有一定难度。二是许多法治改革方案还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予以支持,也有一些重大改革遇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三是法治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从“物理变化”到“化学反应”的过程。所有的法治改革,寄希望今天出方案,明天就完全落实落地是不现实的。我们要允许它有一个不断推进、落实的过程。一定时期以内法治改革越深入,对法律实施的要求就越高、越严、越紧迫。
第五,在总结经验上深化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改革之路,取得了许多好的经验,创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需要长期坚持。同时,在法治改革的一些具体问题上,经过一系列的试点、实验、推行等等,取得了不少改革成果,创造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有的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发现了一些问题。进一步深化法治改革,需要全面系统深入总结前一阶段改革的经验。实验成功的,全面推开;遇到困难的,想办法克服;有的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可以及时调整完善改革方案。这是目前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不是一个小事,可以说是关系到法治改革继续深化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工程。
第六,在提升理论上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有十几亿人口和几千年文明史的大国,大力推行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历史性变革实践,是难得的“含金量”很高的理论“富矿”。习近平法治思想正是根植于此而形成的。这一富矿开创的新时代法治中国之路、中国之治,蕴含着丰富的“中国问题”、自身经验和理论源泉。我们应当在法治改革实践中,下大力挖掘、认真提炼升华,形成科学的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力的法治理论体系,为进一步深化法治改革,大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提供理论指引,作出应有贡献。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原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江必新,中国行为法学会会长董治良,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甘藏春,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会长胡云腾,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中国法律援助和司法行政英烈关爱救助基金会秘书长张建华等到会并发表讲话。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期刊研究会副会长秦前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顾问胡建淼,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商业法研究会副会长刘俊海,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邢会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顾问王晓晔,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叶静漪,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讲席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孙佑海,浙江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双聘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春晖等十位国内著名法学专家分别发表专题演讲,从法学各领域分别阐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法治实施的重大关系。
责任编辑:欧阳雪